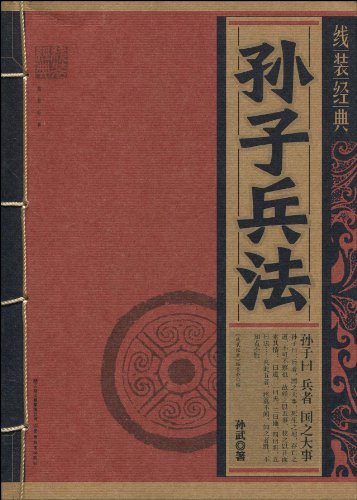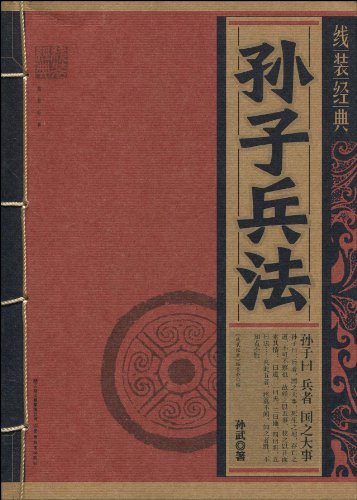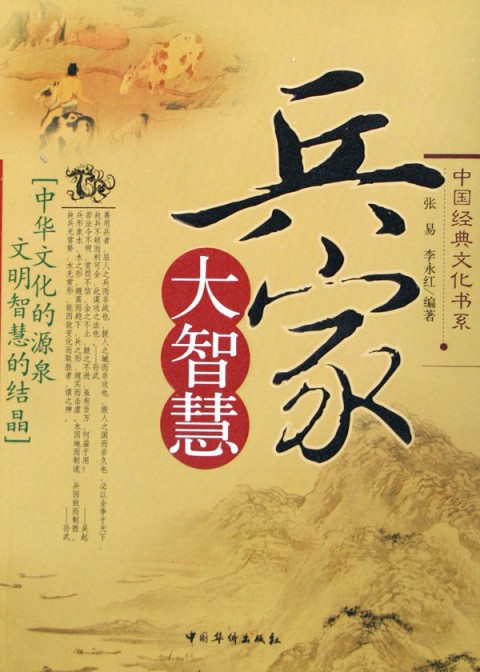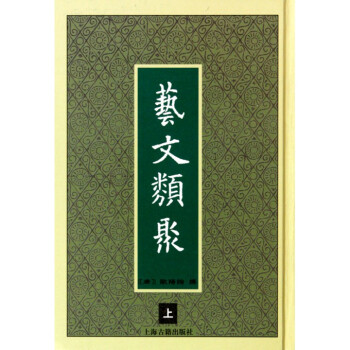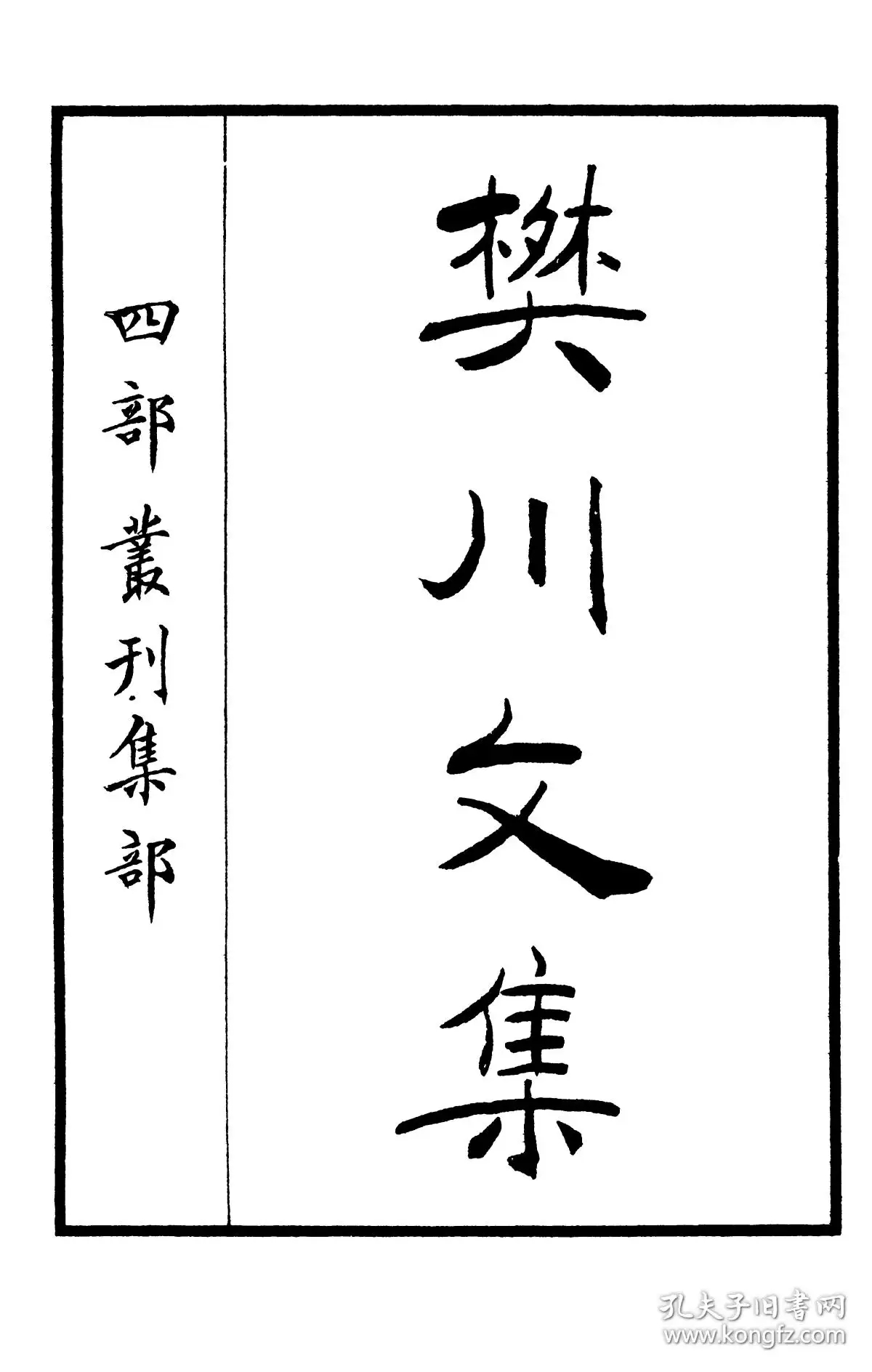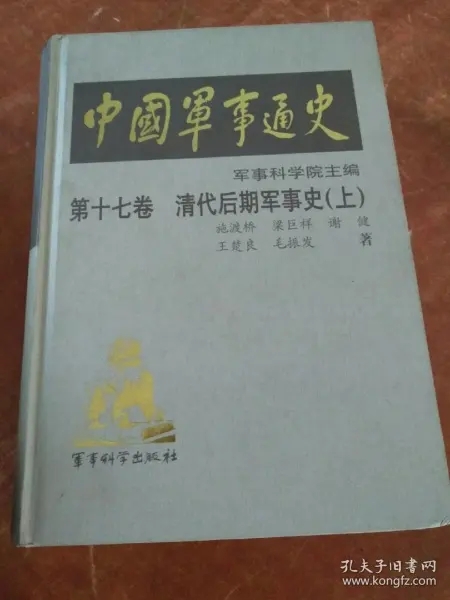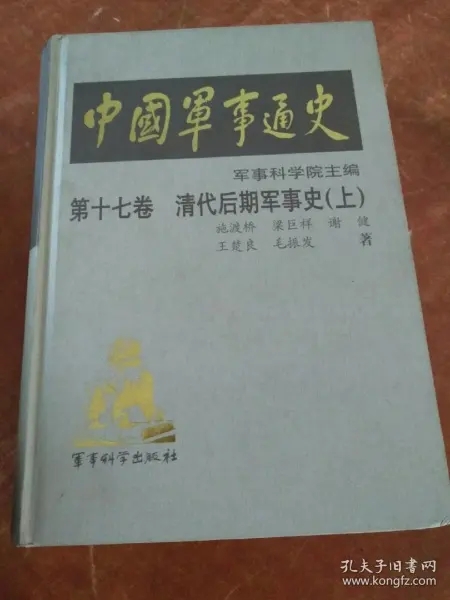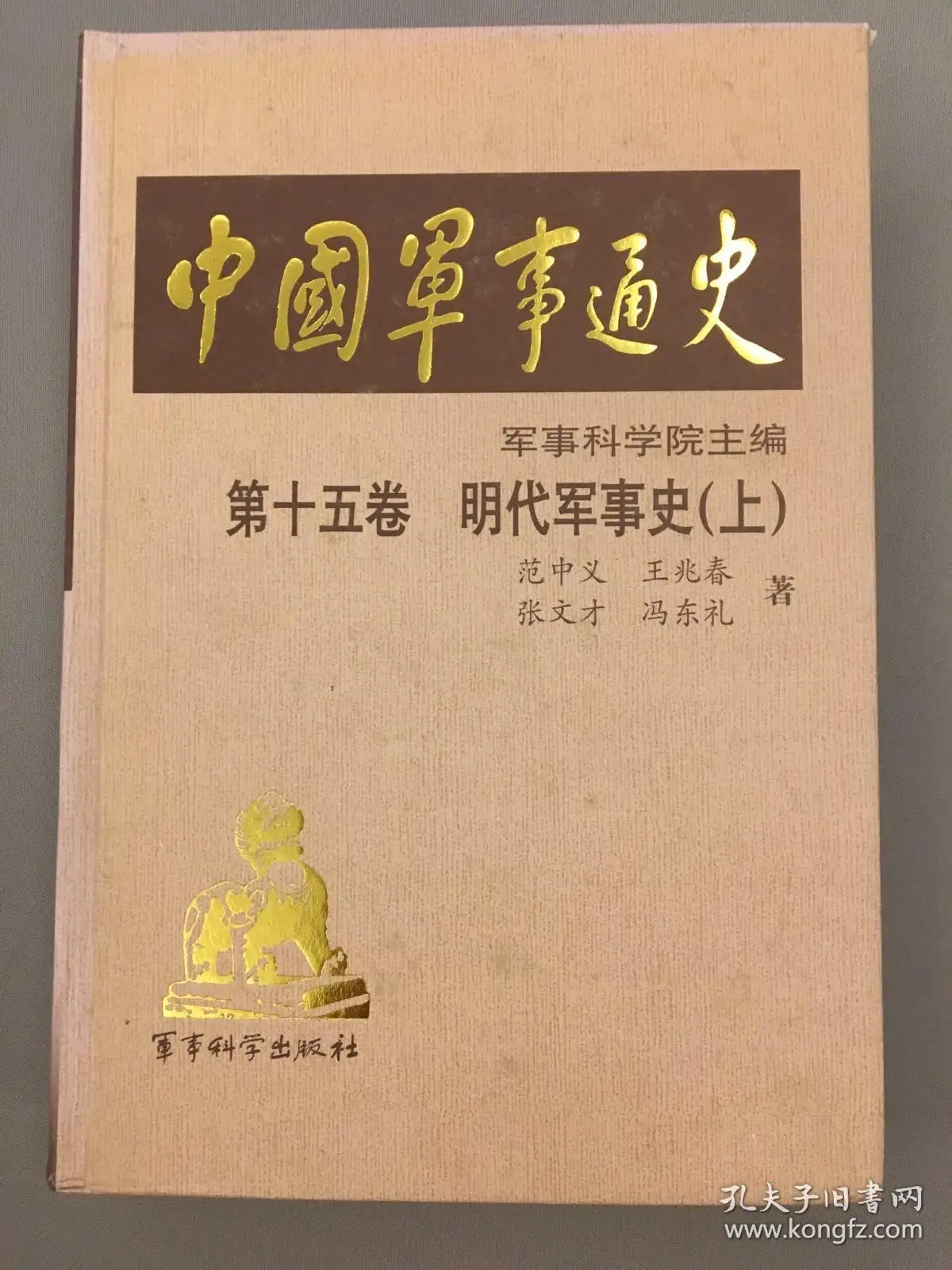孙子兵法 孙子简介 战略运筹 作战指挥 战场机变 军事地理 特殊战法 孙子兵法日文版 日文自序 战略运筹 作战指挥 战场机变 军事地理 特殊战法 孙子兵法英文版 战略运筹 作战指挥 战场机变 军事地理 特殊战法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 十一简介 战略运筹 作战指挥 战场机变 军事地理 特殊战法 施�...
450本兵书,全网唯一最全兵法电子书集合下载(188元/套) 微信(15074818522)添加备注:兵法
吴起兵法网·使命 兵家 兵家四派 兵家四圣 武庙十哲 古代十大兵书 宋武庙七十二将 鬼谷子经典语录 二十条兵家大忌 古代兵家必争之地 中华历代名将谱·上 中华历代名将谱·下 孙子兵法十大经典语录 世界三大兵书经典语录 中国十大兵书及兵书大全 杂谈·孙子兵法注解·始计篇·第一 历代兵书的特点 中外兵书的交流 ...
战争论 论战争的性质·第一 论战争理论·第二 战略概论·第三 战斗·第四 军队·第五 防御·第六 进攻·第七 战争计划·第八 海权论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欧洲的冲突 亚洲的问题 美国的利益 制空权 第一部·制空权 第二部·未来战争的可能面貌 第三部·扼要的重述 第四部·19XX年的战争 谋略 总体战 。 ...
中国战略思想史 自序 先秦时代 秦汉时代 中古时代 元明清三代 西方战略思想史 自序 古代 中古时代 启蒙时代 近代·上 近代·中 近代·下 国防论 国防经济学·第一 最近世界之国防趋势·第二 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第三 二十年前之国防论·第四 十五年前之国防论·第五 。 中国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卷·欧洲的战争 第一部·在波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序曲 第二部·法国的失败 第三部·英国孤军作战 第二卷·世界大战 第一部·大德国 第二部·日本的大东亚 第三部·战争的分水岭 第三卷·意大利的失败 第一部·盟国的战争机器 第二部·意大利投降 第四卷·德国战败 第一部·盟国的攻势 �...
艺文类聚·武部 作者:唐·欧阳询等编纂 出自————《艺文类聚·武部》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将帅 战伐 ◇将帅 《春秋元命苞》曰:上天一星为郎将。 《六韬》曰: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张盖,出隘塞,犯泥涂,将必下步,士卒皆定,将乃就舍,炊者皆饱,将乃敢食。 《左传》�...
艺文类聚·军器部 作者:唐·欧阳询等编纂 出自————《艺文类聚·武部》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牙 剑 刀 匕首 铗 弓 箭 弩 弹 槊 ◇牙 《兵书》曰:牙旗者,将军之精,凡始竖牙,必以刚日,刚日者,谓上剋下也,立牙之日,吉气来应,大胜之徵,《黄帝出军决》曰:始立牙之日,旗幡指敌,或从�...
罪言 作者:唐 杜牧 出自————《杜牧樊川文集》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中书舍人杜牧字牧之 罪言国家大事,牧不当官,言之实有罪,故作《罪言》。 生人常病兵,兵祖于山东,胤于天下,不得山东,兵不可死。山东之地,禹画九土,曰冀州野。舜以其分太大,离为幽州,为并州,程其水土,与河�...
原十六卫 作者:唐 杜牧 出自————《杜牧樊川文集》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十六卫 国家始踵隋制,开十六卫,将军总三十员,属官总一百二十八员,署宇分部,夹峙禁省,厥初历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观之,设官言无谓者,其十六卫乎。本原事迹,其实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贞观中,既武遂文,内以十...
战论 作者:唐 杜牧 出自————《杜牧樊川文集》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战论并序 兵非脆也,榖非殚也,而战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战论》焉。 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珠玑苟无,岂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俭风浑,淫巧不生,朴�...
守论 作者:唐 杜牧 出自————《杜牧樊川文集》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守论并序 往年两河盗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国家不议诛洗,束兵自守,反条大历、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辈益横去声,终唱患祸,故作《守论》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钺钝,含引混贷,煦育逆孽,�...
燕将录 作者:唐 杜牧 出自————《杜牧樊川文集》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燕将录 谭忠者,绛人也。祖瑶,天寳末令内黄,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刘济与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契丹路。后将渔阳军,留范阳。 元和五年,中黄门出禁兵伐赵,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师不跨河二十五年�...
注孙子序 作者:唐 杜牧 出自————《杜牧樊川文集》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注孙子序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据案听讼,械系罪人,笞死于市者,吏之所为也。驱兵数万,橛其城郭,系累其妻子,斩其罪人,亦吏之所为也。木索兵刃,无异意也;笞之与斩,无异...
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 作者:唐 杜牧 出自————《杜牧樊川文集》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 伏睹明诏诛山东不受命者,庙堂之上,事在相公。虽樽俎之谋,筭昼已定,而贱末之士,芻荛敢陈。伏希舍其狂愚,一赐听览。 某大和二年为校书郎,曾诣淮西将军董重质,诘其以三州�...
上李太尉论江贼书 作者:唐 杜牧 出自————《杜牧樊川文集》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上李太尉论江贼书 伏以太尉持柄在上,当轴处中,未及五年,一齐四海,德振法束,贪廉懦立,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匪其任。虽九官事舜,十人佐周,校于太尉,未可为比。 伏以江淮赋税,国用根本,今有大患�...
上周相公书 作者:唐 杜牧 出自————《杜牧樊川文集》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上周相公书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乱者,未有暴乱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国家者,自生人已来,可以屈指而数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诗·大雅·维清》,奏《象舞》之篇,�...
贺平党项表 作者:唐 杜牧 出自————《杜牧樊川文集》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贺平党项表 臣某言。伏奉三月二十七日来,党项剪除,北边宁静,华夏同庆,道路欢呼,臣诚庆诚抃,顿首顿首。伏以上天有震耀杀戮,王者有攻讨诛夷,是以不暂讨者不久宁,不一劳者不永逸。伏以自古夷狄处中华,未有不...
贺生擒衡州草贼邓裴表 作者:唐 杜牧 出自————《杜牧樊川文集》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臣某等言。伏见湖南团练使奏,生擒衡州草贼邓裴及徒党等。伏以湖湘旱耗,百姓饥荒,遂有奸凶,敢图啸聚。今承擒灭,已尽根株,臣等诚欢 诚抃,顿首顿首。 臣闻三代之英,两汉之盛,奸宄乱常之类,挻灾构�...
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 作者:唐 杜牧 出自————《杜牧樊川文集》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某启。伏以圣主垂衣,太尉当轴,威德上显,和泽下流。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星辰顺静,日月光明,天业益昌,圣统无极。既功成而理定,实道尊而名垂。今则未闻纵东山之游,乐后园之醉,惕惕若不足,兢兢而如�...
内容提要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世界古代后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本书用生动而清晰的文笔,有主有次并有点有面地介绍和分析了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5世纪全世界范围内各种典型的军事制度、军事改革、军事思想、武器装备和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战争和战役。如古代罗�...
一、概述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世界古代后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概述 进入世界古代后期,全球各地区逐渐从各种类型的城邦走向统一的专制帝国。因此,这一时期的历史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景象。自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5世纪,在古代希腊、罗马、埃及、西亚、南亚�...
二、共和时期的罗马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世界古代后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二、共和时期的罗马 古代罗马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王政时代、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王政时代指的是从罗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直到建立共和国这一时期;共和时代指的是从...
三、帝国时期的罗马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世界古代后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三、帝国时期的罗马 公元前30年,屋大维(即奥古斯都)在战胜自己的政敌之后,成为罗马的全权统治者,确立了个人的独裁统治,实际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罗马共和制灭亡,进入帝国�...
四、古代西亚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世界古代后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四、古代西亚 古代西亚主要指西南亚,它包括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等。在这片广大的地区,先后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奴隶制国家。其中,两河流域南部...
五、秦汉时期的中国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世界古代后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五、秦汉时期的中国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中国领土上诸侯割据称雄的分裂局面,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一秦王朝(公元前221年一公元前207年)。之后,秦始皇北击匈奴,南平�...
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世界古代后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地方豪强势力不断壮大。起义被镇压之后,东汉王朝已无法维持对全国的统治,统治集团内部外戚、宦官斗争激烈,被豪强势力利...
七、古代印度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世界古代后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七、古代印度 进入古代后期的印度,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战争之后,逐渐结束了前一时期列国并立的分裂局面,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君主专制帝国一孔雀帝国,使印度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期间鼎�...
内容提要 作者:龙源 于可 出自————《世界古代中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古代中期(公元前8一前3世纪)是奴隶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奴隶制国家普遍兴起的时期,人类文明已越出少数几个地区向周边扩展。战争便成为这种扩展的重要手段。各种战争多达2000余次。 地中海世界的硝烟是�...
一、概述 作者:龙源 于可 出自————《世界古代中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概述 1、古代中期的军事交锋 古代中期(公元前8一前3世纪)是奴隶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奴隶制国家普遍兴起的时期,人类文明已超出少数几个地区,向周边扩展。中国的文明已从黄河流域传播到长...
二、古希腊城邦时代的军事 作者:龙源 于可 出自————《世界古代中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二、古希腊城邦时代的军事 古代希腊的地理范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的诸岛屿、小亚细亚沿海地区、意大利南部以及西西里岛东部沿岸地带。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进�...
三、亚历山大帝国的军事 作者:龙源 于可 出自————《世界古代中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三、亚历山大帝国的军事 正当希腊城邦陷于危机、内争不休时,地处北部边陲蛮荒之地的马其顿崛起。公元前4世纪中期,腓力二世(公元前359一前336年在位)执政,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在底�...
四、古罗马共和国前期的军事 作者:龙源 于可 出自————《世界古代中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四、古罗马共和国前期的军事 罗马最初为意大利半岛第伯河南岸一小城邦。约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进入王政时代(公元前753一前510),即军事民主制时期,在此期间,曾一度受到伊达拉里亚人�...
五、亚述军事帝国 作者:龙源 于可 出自————《世界古代中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五、亚述军事帝国 亚述人是西亚塞姆语系的一支,约于公元前三千年代中后期,在两河流域北部以亚述城为中心建立国家,实行贵族寡头政体,尔后过渡到君主制。该国延续二千余年,在与周边各国抗衡...
六、波斯帝国的军事 作者:龙源 于可 出自————《世界古代中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六、波斯帝国的军事 亚述帝国灭亡后,新巴比伦王国和米底王国共同主宰西亚,但它们也只是昙花一现,旋即被伊朗高原东南部的波斯帝国(公元前6一前4世纪)所吞并。波斯原为米底属国,至公元前6世�...
七、公元前8一前3世纪印度的军事 作者:龙源 于可 出自————《世界古代中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七、公元前8一前3世纪印度的军事 古代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地理版图包括今日的整个南亚次大陆。古代印度的历史分期,包括印度河文明时代、吠陀时代、列国时代和帝国时代四�...
八、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 作者:龙源 于可 出自————《世界古代中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八、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 东周始于周平王(公元前770一前720)东迁洛邑,一般以公元前476年为界,分为春秋(公元前770一前476)与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两个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时代由...
九、中外军事比较 作者:龙源 于可 出自————《世界古代中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九、中外军事比较 矛与盾的碰撞构成了世界各国古代中期军事争伐的主旋律。为了战争,各国都组建了强大的军队,先后用铁制武器取代了铜兵器,使用诸种兵制以保证兵源,并运用了各种军事奇谋无论...
结语:对人道的呼唤 作者:龙源 于可 出自————《世界古代中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结语:对人道的呼唤 公元前8一前3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充满血腥战争的世界,一次战争杀人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残杀战俘被视为理所当然。汉尼拔曾一次屠杀罗马战俘5000余人。白起于长...
内容提要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世界古代前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内容提要 军事史是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历史。在最早的奴隶制国家里,军事战争构成了从奴隶制城邦到一统大国,最后达于帝国发展史的强有力的主旋律。古代中国很早就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征兵、教...
一、概述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世界古代前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概述 1、古代世界军事文明的巨大发展 在古代社会的早期,人们在世界领域内的广泛来往和交流是不存在的,他们只能生活在自己周围的狭小区域内。即使建立起疆域广阔的奴隶制大帝国,他们也�...
二、原始军事萌芽与战争的起源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世界古代前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自从人类出现以后,人类与生物界接触发生冲突时,人体自身就是人类第一种冲击和防御武器,牙咬、拳打、脚踢、手指抓挠以及拳挡、足跑等。人类在何时第一次诉诸战争,由于什么原因发�...
三、古代埃及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世界古代前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1.、前王朝与早王朝时期埃及文明的开始 古代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尼罗河下游,其基本区域是沿尼罗河两岸的一个狭长地带,地理范围大约和今日的埃及国家相当。从希腊时代起,西方人就知道埃及是�...
四、古代西亚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世界古代前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1、苏美尔文明两河文明的源头 (1)苏美尔城邦的形成 两河是指亚洲西南部注入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古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意即“河间之地”�...
五、古代印度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世界古代前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1、印度河文明时期军事的萌发 古代印度主要包括今天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领土,在古代文明中是仅次于中国的大国。可是在古代,南亚次大陆从未得到统一过,在它领域内的大小国家也没�...
六、古代中国(夏、商、西周)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世界古代前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1、夏朝中国古代文明的开始 (1)启建夏与甘之战 夏王朝的建立者为启,实际在启的父亲禹之时就已为他打下了立国的基础。禹早年率领民众治水有大功,提高了自己的声望,晚�...
七、古代希腊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世界古代前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1、古代希腊文明的出现与特洛伊战争 (1)爱琴文明的出现与希腊文明的滥殇 古代希腊的地理范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东面的爱琴海和西面的爱奥尼亚海的群岛和岛屿,以及今土耳其西南沿�...
八、早期与共和时代的罗马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世界古代前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1、罗马国家的形成与塞维军事改革 (1)伊达拉里亚文化罗马文明的源头 古代罗马国家的中心地区是意大利,它的地理范围包括意大利半岛及其南端的西西里岛,罗马城则位于半岛�...
本卷提要 作者:杨东梁 张浩 著 出自————《中国清代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清代军事史》叙述了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一一清朝在军事方面发展、变化的历史。其中不但包括清王朝从1644年(清顺治元年)定鼎北京至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被推翻共268年的军事活动内容,也追溯到了1616年(明...
一、清代军事概述 作者:杨东梁 张浩 著 出自————《中国清代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清代军事概述 有清一代在我国历史上,是由少数民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有数的王朝之一,它统治辽阔的中国达268年之久。建立这个封建王朝的满族是一个矫健、骁勇的民族,保持着一种强悍、...
二、清前期的战争和军事思想 作者:杨东梁 张浩 著 出自————《中国清代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二、清前期的战争和军事思想 满洲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统一中国的进程主要是通过战争进行的。清前期的战争主要是入关战争和统一战争。其中清与南明的战争是明、清政权争夺封建...
三、乾、嘉时期的战争 作者:杨东梁 张浩 著 出自————《中国清代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三、乾、嘉时期的战争 乾隆、嘉庆时期的战争主要是巩固统一和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这一时期,清朝国力极盛于一时,清朝统治者通过战争完成了前期在巩固边疆中未竟的事业。中国疆域的基...
四、晚清时期的战争和军事思想 作者:杨东梁 张浩 著 出自————《中国清代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四、晚清时期的战争和军事思想 所谓晚清时期,在这里指的是从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起直到清朝灭亡为止的一段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清朝统治已腐朽不堪,随着殖民势力的入侵,中�...
五、清代的兵制 作者:杨东梁 张浩 著 出自————《中国清代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五、清代的兵制 (一)兵制概况与沿革 从顺治元年(1644年)至宣统三年(19......
六、清代的军事经济 作者:杨东梁 张浩 著 出自————《中国清代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六、清代的军事经济 (一)军事经济制度 1、八旗兵的旗地、粮饷制度 &nb......
七、清代的军事教育 作者:杨东梁 张浩 著 出自————《中国清代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七、清代的军事教育 (一)清前期的军事教育 满洲兴起、发展以及统一中国,都......
八、结语 作者:杨东梁 张浩 著 出自————《中国清代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八、结语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个王朝统治的时期,已处于封建末世,中国社会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没有新的生产力,自然不可能向资本主义转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不�...
本卷提要 作者:毛佩奇 王莉 出自————《中国明代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本卷所叙述的是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弘光元年(1645年)共277年的军事史。但它上溯到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义,下延到南明各小朝廷。 明朝面对南倭北虏内忧外患,设置了庞大的军事机器,皇帝首先要保证它确凿无误地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