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作者:阿里安·古罗马
出自————《亚历山大远征记》
出自————《战争通史》
本书正文系以笛杜所编杜勃纳抄本为依据,而杜勃纳抄本是以巴黎手抄本为依据的。前者一般简称A抄本,后者简称B抄本。B抄本,即十五世纪巴黎古抄本(1753年)和十五世纪君士坦丁堡稿本(一般简称C稿本),几乎可以肯定是直接根据A抄本原稿而来。而且因为其脱漏(卷七12.7)实际上是A抄本的一整页,所以罗斯认为A抄本是最原始的抄本。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A抄本,即十二世纪或十三世纪初的温杜包尼西斯古抄本,后曾有人校正,于是又产生了A2抄本,或称K抄本,亦即格罗诺的“最好的佛罗伦萨古抄本”,这个抄本杜勃纳也曾利用,他极重视B和K两种抄本的一致。由于纸页散失或毁损,A抄本有脱漏;而所谓“第二批”手抄本一般也有许多小脱漏。因此,只有将B,C及K(由A2而来)合并使用,才可避免脱漏(只有卷七中的共同漏页除外)。
A和B两种抄本的《印度》一卷最好。阿里安企图仿效希罗多德的格调,这是值得赞赏的,但有时也有错。
因此,编辑《远征记》的工作是比较容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忽视通常的校订方法。应当指出,编者往往发生一些偏向,其中有两个是主要的:其一是,尽量使阿里安“典范化”,这是很自然的。阿里安的时态往往不合规则,已完成的动作他常用未完成时;他的介词有时用得很奇怪,甚至用表示“上溯” [ 罗布出版社编者注:卷二(一)3 ] ,他的和用的不是地方,而且也不是经常和它的一致。克勒格和辛提尼斯为了纠正他这些错误下过很大功夫。他们所以这样校订的基本思想是,他们认为希腊人一贯运用他们完美的语言工具。此外,阿里安还常常为了把话说明白,写了许多不必要的、重复的字句。这样就形成了大批“相同的语尾”,于是有时造成混乱(参见卷一[十二]),有时容易使人怀疑有遗漏——尽管这些遗漏一般都是很小的。由于他的和 [ 罗布出版社编者注:卷一(七)2 ] 和一般用法不同,也引起同样的怀疑,总的说来,我反对编者在原著中插入一些语句,我更完全反对任何“典范化”的倾向。如上所述,B,C和K三种稿本结合使用,已可以避免“第二批”抄本中的许多脱漏。在缺少A抄本的情况下,我们改用和它相同的A2抄本(即K稿本)与B抄本,加上L稿本(十五世纪劳润田抄本,据罗斯说,它是“第二批”手抄本中最好的代表本),就不致发生错误。诚然,我曾尽量利用罗斯的考证材料(1907年小杜布诺编)。不过,他有些建议虽然很有意思,但根据罗斯本人对抄本的估价看来,并不是有必要的,因此我并未采用。对专名的各种变异(除所指系不同的人之外——如卷四[十九]2、[二十一]1、[二十二]1)也是这样。对苏伊达斯和攸斯塔西亚斯提供的证据,对在坡利欧塞提卡发现的不一致的材料(卷二[十五]和[二十五],围攻提尔和加沙)我照例也都未采用。再者,字形的准确当然是重要的,但当人们无法断定的地方(例如卷一[二十一]4关于和),而且译文也并非不自然时,我都未离开手抄本。因此,阿里安的过去完成时就成了愿意打笔墨官司的人们争论的重点。不过,不论科伯特还是洛伯克,除了说阿里安应当这样或那样写之外,并未给我们更能令人信服的东西。此外,至少有一个专名的写法也弄错了(卷二[十二]2里的),还有些人的父亲的名字不对,有些历史和地理情况的解释也有错误。这些错看来是属于阿里安的,并不是抄稿的人抄错的。抄稿的人也偶尔把数字抄错(如卷二[二十七]3)。
谁想得到整个考证资料,就可以参考罗斯整理的那些。我在这里特地对他表示感谢。他的考证(包括波拉克的考证)中具有扎实的、而且往往是高明的见解。但由于这样的校订本是不可能翻译的,至少是很难翻译的,而阿里安这本“远征记”在校订艺术方面也并不是引人入胜的,也只得以这个不完整、不准确的形式问世。
我只对卷一(一)段6节提出了我个人的意见。
版本、译本及其他
《远征记》的版本,除格罗诺版本外,还有阿比其特1875和1889年版本,克勒格1835年版本,辛提尼斯1867年版本,罗斯(小杜卜诺编)1907年版本。H·W·奥顿(布莱克伍德)还编写了卷一和卷二的学生版(1902年),否则,这么有意思的一位名家著作就没有学生版了。秦诺克(E.J.)的《远征记》和《印度》译本,附有一些有用的注释,但现已绝版。在巴黎出版的一套很好的名著(原文和译文,G·布德学会编)中,也有《印度》这一部。
在J·W·麦克润德所著《古印度史》五卷中,大段大段地摘录了《远征记》和《印度》中的文字,译文很好。还可参见《剑桥古代史》卷六(W·W·塔恩著)、《剑桥印度史》以及《英国历史杂志》1896年十月号中白尔汉姆的文章。在一般学术杂志和年鉴中,阿里安不大引起学者注意。近年出版的卜西安年鉴只提到几句。《希腊研究杂志》近几年来有过一些有意思的摘要(W·W·塔恩在48期[2],L·R·太勒在47期[1]和48期[1]有一篇叫《波斯王的精灵》;A·D·诺克在48期[1]有一篇文章,探讨亚历山大以前的“对统治者的崇拜”即关于“匍伏礼”的问题。这下子当然引起了争论。但我们可以怀疑,就连亚历山大本人也不见得很明白这种事会招致什么后果,或可能招致什么后果)。关于阿里安著作一般是否可靠的问题,在这些文章里也进行了大量的讨论。
阿里安(FLAVUS ARRIANUS)
阿里安一生的经历比较简单。他是希腊人,约于公元96年出生于尼考米地亚。因此,当哈德良、安敦尼·庇护和马可·奥理略 [ 译者注:他们都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当时希腊已经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 在位时,正是他在世的时期。哈德良曾委任他为卡帕多西亚总督(公元131-137)。对一个希腊人来说,这个职位已是最高的荣誉。147年他在雅典当执政官。阿里安大约死于180年。由于曾在部队服役过,所以他写这部远征记的时候还是一位行家。作为艾皮克提塔斯 [ 译者注:(约公元55-135),雅典斯多噶(禁欲主义)学派的哲学家 ] 的学生,他曾把老师的讲话记录下来编写成书,即《师门述闻》。在他的老师的学说方面,他算是一位重要权威。
他写的这部亚历山大历史的价值取决于当时的官方史料是否准确。而官方史料是否准确这个问题却是无法解决的(正象W·W·塔恩在《剑桥古代史》卷六中指出的那样)。因为阿里安并不隐瞒他写的这部书是以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拉斯二人的记述作为主要的依据。关于前者,他还曾天真的说出他的看法,认为托勒密作为国王不至于说谎;甚至还说,托勒密写书时亚历山大已经死去,他再吹拍谄媚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阿里安这个看法只能说明他尊敬帝王,也许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但同时也说明他缺乏批判精神。亚历山大死后,托勒密把他自己在远征中扮演的角色加以美化,满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好处。马哈菲在他的《希腊生活和思想》第205页上说:“在托勒密的记述中……很明显,他对自己的成就毫不挑剔,也毫不遗漏。”在同页的脚注中还补充说:“作为一位作家,托勒密(苏特)的命运是稀奇古怪的。一方面有阿里安夸奖他的《亚历山大回忆录》是一部最严肃、最真实的著作;另一方面,有人杜撰了一些故事,冒用卡利西尼斯 [ 译者注:亚历山大的随军御史,朝廷大事和远征情况都由他编写。 ] 的名义发表,后来在书前还加上托勒密的名字。而且,在C·米勒所著《伪卡利西尼斯考》一书的序言第27页上,还有一位中世纪的读者写的一首讽刺短诗,描绘托勒密的无知和欺诈。”
托勒密究竟是不是一只寻觅狮子吃剩的残肉碎骨以果腹的豺狼,我们可以先不去管它,也可以认为中世纪那些讽刺短诗不足为凭;但问题并非就此结束。假如说托勒密所记述的亚历山大的进军和胜利应是准确的官方史书的话,那么,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是否仍然是准确的呢?而阿里安写的历史显然是以托勒密作为主要的根据。
读者对这个问题将有机会得出自己的看法。因为在阿里安的著作中,读者可以读到他那些小小的自我流露和他自己发表的意见。当他感到义不容辞时,他能毫无顾忌地对亚历山大本人进行严厉的批评,这是值得赞扬的。在军事方面,虽然他有些专长,而且把亚历山大惯常的军事调度写得很清楚,但一出现不平常的情况,他写的东西就有些含糊不清。一般说来,他写的历史还是读得下去的,只是有些单调沉闷。但当他根据两种或更多的史料编写时,往往不能把它们很好地揉合在一起。当然,这是古代史作家的通病。
他对亚历山大一生中那些浪漫主义色彩的东西,大部分都清醒地避开了。考虑到这么伟大的军事业绩只有少得可怜的文献记录时,他这样做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亚历山大的部队、战术和阿里安的术语
我们感到幸运的是,亚历山大的战术属于最简单的一类,但颇有效力,特别在对付“土著”部队时。他的兵力重心是“方阵”,右翼是装备最重的骑兵精锐,左翼是其他骑兵。在右翼外侧(也许在左翼外侧)是弓箭手和其他轻装部队。全部兵力的实际运用因地形不同而各异。但在一般的地形上,亚历山大通常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位置时,左翼开始时只是坚守阵地,中央作为右翼的坚强枢纽,右翼则冲击敌人的左翼(或叫“盾牌一边”),甚至常把敌人赶到中央受方阵长矛杀伤,或赶到左翼受到骑兵长枪的冲刺。阵线中央的方阵对付敌人主力,但一般不前进太远,除非右翼惯常的迂回受阻或发生异常情况。
但阿里安对亚历山大的部队和战术的描述并不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他确实也不是在同样情况下用同样的术语。他常用的专门术语,按顺序说就是,和。原义应该是部队一部,即持长矛的步兵,但有时他又用以代表全军。的下属建制就是,这个字有时用作专门术语,有时则不然。这些可能是按部队招来的不同地区组织的。这个字特别麻烦。它显然常常没有什么特定的意义。在上边引用的复合字里,它的意思就象我国“本土部队”,指部队人员互相都认识,都是同伴或同乡。但这种部队当中有一部分(实际上都是由真正马其顿出生的人组成的部队)配属亚历山大本人,作为他的近卫队的一部分。阿里安用“伙友”这个字眼时是否想让我们理解为“(亚历山大的)伙友”,这一点还搞不清楚。但他用这个字又作为一种头街,就象他用或似的,意即“国王扈从”,也许是“(马其顿)贵族子弟”。除这个字根外,不论或,都有,这个名词一般指的是轻装(护身装备较轻的)部队,也指某种附属部队(以其特殊名称表示),但也包括或雇佣兵,即由塞萨利、包欧提亚等地的人组成的部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阿格瑞安人组成的部队,他们是了不起的山地战和前哨战的能手。
现在我们谈谈一种规模很大的部队,也涉及。这种部队组成亚历山大的卫队和实际上的近卫人员。最近身的可能是“扈从”,这些人也形成他的幕僚。再就是精选的,再就是(从广义上来说还有),叫作,也许和相同。但这支叫作“近卫”和“卫队”的大部队,并不只是保卫他们那位英勇的、甚至是鲁莽的领袖,而宁可说是形成一支特殊的突击队,极其机动灵活,随时准备突然急行军或去完成危险的突击任务。
军队的调度是这样。方阵即使不是永远成方形,至少也是成长方形的。在下图中可以看到这几个专门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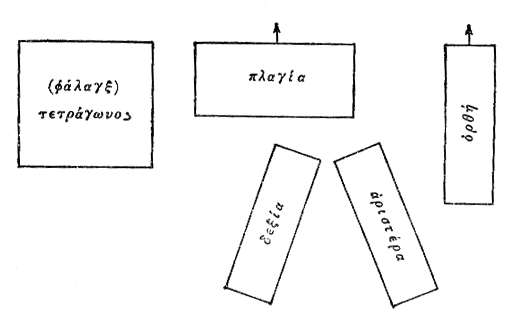
方阵并不是象历史家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僵化的队形。它可以象上图所示的那样拉长(就是这个意思),成为长方形,也就是形成摆好的阵势;也可以收缩(),以便突破敌阵。
但是,如果估计敌人要包抄,方阵就可以拉得很长(就象在高伽米拉战役中那样)。中央可以向前突出,从而形成两个正面(左右两个斜面)。如果方阵本身准备包抄敌人,则中央又可成凹形。方阵有时还可以成楔形或箭头形,,但必须记住,不能成封闭的楔形。最紧密的队形是,“盾牌挨盾牌”。
侯加斯博士在他的《腓力和亚历山大》一书中对马其顿部队有一段有价值的描述,对他较早出的一本小册子里的说法作了些修改。
本社所组译出版的 Aenaeas Tacticus 等书可能提供一些帮助。但参考时要谨慎。这些书并不能确切地代表我们的时代。
地理注释
在任何一本严肃认真的地图上,亚历山大远征路线的大部分都能找出来。至于他为什么选择这些路线则并不总是容易理解的。
奥瑞尔·斯太因爵士在《地理杂志》1927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号上发表的文章和所著《亚历山大向印度河进军的路线》一书(1929年麦克米兰版)中,都说他发现了阿尔诺斯山的确切地点。这件事近来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他说这座山在皮尔萨尔(Pir-s’ar)山脉上,在印度河的一个河湾内,河道西边(即右岸),在干南加尔正北,卡克达拉东北。
这条山脉很符合阿里安描述的情形,只是(对一个没见过实况的读者说来)那地方似乎养活不了象阿里安所说的那么多人口。
更严重的问题是,阿里安的描述是否准确。我们一直感到亚历山大沿印度河向上游走这么远似无必要。倒是有人怀疑他往北走可能是为了寻找某个山谷或关口,但未能找到,反而被某一好战部族拦住。他们守住自己的卫城,亚历山大费了事先没有估计到的很长时间才把他们轰跑,后来他又回到南边。于是他那些耍笔杆子的追随者们就不得不为他的部队转变方向和受到阻拦的情形找借口,因此就为亚历山大攻击这个特殊的山杜撰了许多特殊的理由。
我们也许只能这样说:假如阿里安所说的情况是准确的话,那么奥瑞尔·斯太因爵士指出的这个地址几乎就可以完全肯定是没有错的。
